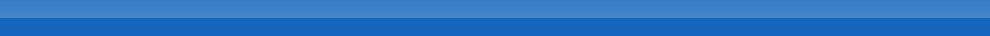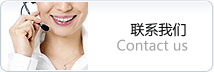
QQ:756851501

48年前,同是孤儿的13岁的瓦志言、18岁的普四言和17岁的邓加,结伴踏上投靠缅甸亲友的道路。

家人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帮发烧的阿起退烧,没有医保的人们总是讳疾忌医,每当生病,他们要先尝试下自己的土方。
10月15日是一个晴朗的周一。72岁的普加和村里人在教堂一起吃完今年感恩节的最后一餐后,准备爬45分钟的山路回家。
教堂在高山上,几十米开外,是千米高的怒江大峡谷和日夜奔流的怒江。
普加的家,在全村最高的寨子里,那里一共七户人家。从教堂位置,能看到他们的房子。“缅甸人住的地方。”村里人习惯性地说。
普加也习惯了。1958年,18岁的他跟着叔叔徒步两天,翻越高黎贡山,去缅甸生活。在那里,人人说他们是中国人。27年后,他们一起迁回自己的出生地中国。而此时,人们又开始说,“他们是缅甸来的”。
从离乡的那一刻起,他们失去了国籍认同。至今,他的孩子们、他的朋友们,都是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人。
山雨欲来
1958年,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蔓延到怒江福贡边境大山里。“不能被抓进去。”叔叔最终做了个决定,带上普加,翻越西面的高山,逃到缅甸。
从怒江边来到他们的寨子,至少要爬3个小时陡峭的山路。罕有的外来客,让几位老朋友们围坐在火炉旁,一起回忆起五十多年的过往。
这是一间傈僳族传统木屋,靠几十根木头支撑在山坡上,透过竹子编织的地板,能看到架空层圈养的牲畜。所有的空间加起来不过30来平米,普加举全家之力,花了一两年才建好。在这里,他将自己的子女抚养长大,直至女儿们出嫁,儿子们成立了自己的家。
已儿孙满堂的他,心中仍有一大憾事,那就是自己和妻子没有任何户籍证明。现在,除了最小的过继到兄弟家中的女儿有户籍,他的所有子女至今都是无户籍人员。
同寨子的老朋友们无不类似。
聊天中途,80岁的此嘛迈帮同村一病人做完祷告回来了。1958年,他与普加在同一个月去了缅甸,又在1986年同一年回来,至今过了54年无国籍的生活。“我已经老了,无所谓了,唯独担心自己的孩子们。没有户口,什么都办不了。”
他的一句话,引得室内突然一阵沉默。
1958年,是所有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年份,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蔓延到怒江福贡边境大山里。
当时才十多岁的瓦志言清楚地记得,那一年4月的一天,家里突然来了几个人,将父亲带走了。此后,他再没有见过父亲。
18岁的普加父母早逝,叔叔是他和弟弟生活中最大的依靠。“不能被抓进去。”叔叔最终做了个决定,带上普加,翻越西面的高山,逃到缅甸。
几天之后,此嘛迈也孤身上路了。
那是一条他们从未踏过的路,“怕,非常怕,但那时候人比鬼更可怕。”门牙掉光的此嘛迈陷在回忆中,火光照着那张凝重的脸。寨子里的年轻人默默地坐在外围,他们第一次听老人们如此认真地回忆这段往事。
生死通道
50多年来,高山上的人们无数次来回穿越这条通道,有人在12月过山,在大风雪中,被冻死在山上。有人在七八月雨季过山,被洪水冲走。
怒江左岸的山群被称为高黎贡山。福贡县是“幸福的高黎贡山”的意思。生活在山上的边民们却对这个名字很陌生。“米可”是他们知道的唯一山名。那是他们给通往缅甸的山路上需要翻越的最高一座山峰取的名字。
沿着福贡县上帕镇古泉村一条山上小路,一直往西,3个小时后,直至离中缅边境线最近的村寨之一俄沙恰底,爬上寨子背后的最高峰,便能看见人们口中不断提起的“米可”。以米可的山脊为界,另一面便是缅甸。
50多年来,高山上的人们无数次来回穿越这条通道,有人在12月过山,在大风雪中,被冻死在山上。有人在七八月雨季过山,被洪水冲走。
54年前,此嘛迈就穿行在这条通道上。他幼时便成了孤儿,叔叔将他抚养成人。1958年4月,形势越来越出乎人们的预料,村里陆续有人沿着通道出去了。在一个无人注意的早晨,此嘛迈穿了件薄薄的单衣,光着脚便悄悄上路了。灌满水的弓形水壶是他唯一的行李。
那是一条他从未走过的路,不知道路的尽头有什么,不知道要走多久。害怕,但不能回头。好在这条路没有岔路。宽的地方有两三米,窄的地方只容一人通过。很多时候,路的另一边就是悬崖。
从早晨到下午,此嘛迈数不清自己翻越了几座山,一路忐忑,没有遇到一个人影。饥饿难耐,他不停地给自己灌水。
山路越来越陡。快到傍晚时,一座巨大的雪山进入他的视线。他后来知道,那座雪山,就是米可,在四月天里反常地下起了大雪。
此嘛迈不打算在黑暗中翻越雪山。晚上七八点,他终于在米可山下发现了一块可以躺二三十人的岩石。此嘛迈捡了些柴草,打算在岩石上露宿一宿。
这块岩石成了后来通道两边人们最熟悉的地方之一。所有需要穿越通道的人,都要趁天还没黑之前,赶到岩石旁,铺草席露宿。几十年过去,现在的岩石已经不像此嘛迈第一次见到时那么大。不知从何时起,岩石还有了个傈僳名字叫“米可阿杰库”,意思是“米可山下像房子一样大的石头”。
第二天刚亮,此嘛迈再次出发。饥寒交迫中,攀越雪山的双腿一度颤抖。本能的求生欲望支撑着他埋头坚持。
不知过了多久,他发现自己爬上了山顶。十几公里开外,缅甸成片成片的山峰尽收眼底。回头往东,他甚至辨认出自己熟悉的怒江大峡谷。
离缅甸的亲朋不远了,他心想。深吸一口气,一鼓作气冲下山,在太阳落山之前,终于看到了远处的寨子。
同样说着傈僳话的人们,接济了几近昏厥的他。他很快在同一个寨子里找到同村逃难过来的人们。
缅甸居不易
因为地势的关系,大多数去缅甸者在山里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生活,山中没有油,没有盐,没有大米,没有学校,没有医院,生了小病则拖着,生了大病就翻山来福贡。
同一个月,普加和他的叔叔沿着同一条通道,抵达米可山另一边。
那是一个满是高山的地方,和这一面一样,人们在山坡上建房、开垦。不同的是,缅甸的山更多、更陡。
抵达缅甸的第一天,一个陌生人给了普加一口锅,他们就靠着它维持了最初的生活。许多天后他们才知道,这个地方叫新拉达。有近十个小组,近千人左右,但寨子特别分散。从一个寨子到另一个寨子,要爬一整天的山路。距离那里最大的缅甸县城,至少要走十五天的山路。
新拉达村既生活着本土的缅甸人,也有早几十年从中国迁徙过去的傈僳人。面对突然闯入的庞大人流,当地政府一度劝说他们:“你们是中国人,回中国去!”“逃亡者”们大多时候默不作声,只轻声回应:“我们是傈僳人。”
刚刚抵达的前一两年,“逃亡者”们大多寄宿在亲戚朋友家中,边开垦荒地,边建设自己的房屋和教堂。
缅甸有政府,但因为路途太遥远,十多年也不见缅政府过问他们的生活,没人帮他们落户。
1964年,同是孤儿的13岁的瓦志言、18岁的普四言和17岁的邓加,结伴踏上投靠缅甸亲友的道路。
现在,没人能具体统计,1958年开始共有多少边民从怒江翻山去到缅甸。在普加的记忆中,“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人出去,木骨甲村靠近通道,去的人较多,至少有一百多人去了缅甸”。
因为地势的关系,大多数去缅甸者在山里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生活,山中没有油,没有盐,没有大米,没有学校,没有医院,生了小病则拖着,生了大病就翻山来福贡。
几十年间,极少部分人因为做生意攒了点积蓄,搬去了缅甸稍大的城市密支那。大多数人因为没钱,留在高山上。
回家
1986年6月5日,一支近百人组成的迁徙队伍行进在米可山上,队伍中,半数以上是孩子。他们身上只带着水和干粮,所有的家产被丢弃在“新达拉”。
20年间,山的这边一成不变,山的另一边却变了天。
1986年,新达拉村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。他是瓦志言的叔叔。他于1958年和哥哥一起被抓进监狱,不久,哥哥在狱中死亡,他在1985年被释放。
他的到来让全村人惊喜不已。他告诉大家外面的情况,“可以回家了”。这迫使全村人正式直面这个问题。
人们开始盘算回家的方式。几天后,当地村政府告诉他们,要回去可以,但在这里的所有牛羊、房子都无法进行买卖,也不准将财产带回中国。
1986年6月5日,一支近百人组成的迁徙队伍行进在米可山上,队伍中,半数以上是孩子。他们身上只带着水和干粮,所有的家产被丢弃在“新达拉”。
年龄稍大者如普加和此嘛迈等,他们既欣喜又忧虑。几十年来回,他们早已得知,自己曾经居住的房子被拆,耕地被分了。稍年轻者如邓夺、罗四言,他们对山的这边,陌生又未知。仅因为想陪伴父母回归故里,于是也拖家带口大迁移。队伍中的女人们则都任劳任怨。娜前1958年跟随家人去缅甸,几年后和同是逃亡者的邓加结婚生子。“这里是我们出生的地方”。到今天,当人们问她为什么回来时,这是她脱口而出的答案。
6月6日黄昏,迁徙的队伍抵达俄沙恰底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寨子。寨子里的人们在队伍中认出了自己的亲人。另一部分人继续行进,穿过阿亚比,回到古泉、木罗。迎接他们的,是这边的亲人、朋友和教会。
大规模的人口流入惊动了政府。不多久,有人上山来告诉他们,“你们的户籍早已被销掉了,不再是中国人,回缅甸去吧。”此后每隔一段时间,都有人来劝他们回缅甸。但陆续迁回中国的人并未停止。
像在缅甸一样,人们默不作声,只是在有需要时回应道:“这是我们出生的地方。”争吵不可避免。1986年10月的一天,再次有政府人员来劝说他们回缅甸。争执中,瓦志言的前妻因为害怕,突发心脏病,昏倒在家。一个星期后,她去世了。
悲愤,一度笼罩着这群没归属的人们。从那以后,再也没人赶他们回缅甸。
 返回首页
返回首页 加入收藏
加入收藏 网站地图
网站地图